
从《南京照相馆》到《东极岛》,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热映的电影,带着观众穿越回正义最终赢得和平的烽火硝烟之中。有没有想过,在抗战时期的中国影院里,能放映什么样的电影?

9月3日前夕,以“多元视角下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为主题的2025中法论坛,在与上海师范大学为邻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教师教育中心举行。作为电影发明国、拍出《虎口脱险》等经典二战片的电影大国,法国巴黎索邦大学、卡昂大学等文史专家们与中国学者交流,也关注到战时中国电影与电影人,如何演绎战火中的影像与人生。
事实上,1937年之前,以“东方巴黎”上海为中心的中国电影业已相当成熟,不论是影片发行量还是观影人数等,都在亚洲数一数二。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史研究所研究员汪朝光表示,当时世界上电影年产量超过百部的国家,只有五六个,而中国就在其列。
然而,抗战全面爆发之后,中国影业颠沛流离、支离破碎,被“一分为三”。汪朝光认为,其一是仍以上海为中心的“孤岛电影”,受到战争冲击后先在外国租界复苏,但其后太平洋战争爆发,随全城沦陷又变成了“沦陷电影”;其二是从上海转移至武汉、重庆的“后方电影”;其三则是日本实际统治下的“伪满电影”。
除了空间区隔,行业特点各有不同。“孤岛电影”延续着私营影业公司为主、娱乐电影为主的特点。受时局影响,在重压之下,上海电影人也放映一些古装题材影片,比如“花木兰”等,以此暗示抵抗外来侵略,间接参与抗日运动。上海沦陷后,所有电影公司均被收编,组建为“伪华影”,出品一些软化反抗心理的影片。其中,也有少数指向所谓“大东亚共荣”的影片,比如“鸦片战争”等题材,试图以此鼓动民众反对美英等国的情绪。
值得注意的是,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美国电影在华遭禁,日本电影则被批量引进,包括显示所谓“皇军赫赫武功”的题材,在社会文化心理方面毫无同理心,票房均不佳,观众很有限,映期也仅一两天。汪朝光表示,尽管部分上海电影人因为种种原因,没有内迁而留在沦陷区,但他们中仅仅极少数与日方合作,还有一些上海电影人在后方转而投身话剧,在剧院排演剧目。
在武汉乃至重庆等地,受制于器材设备等条件不足,“后方电影”从民营为主变为官营为主,从娱乐化转向政治化,且主题单一,均为抗日题材。但总产量不足30部,不及战前上海一地的年产量。而“伪满电影”受控于日本,该国一些著名电影人几乎都曾在东北工作过,所拍影片也限于单一题材,即宣传并号召民众所谓“中日满亲善”。但这类电影在包括上海在内的关内基本没有市场,受众倾向于观看被禁前的美国电影以及本土电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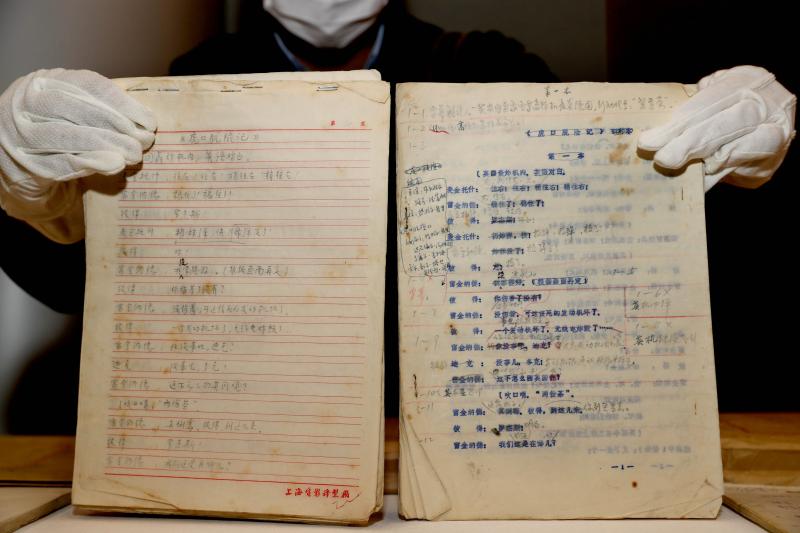
中国学者中也不乏从电影视角理解法国二战史的。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上海抗战研究会副会长马军认为,法国二战电影不太可能按照苏、美模式,拍摄《斯大林格勒战役》《攻克柏林》《中途岛海战《最长的一日》等史诗巨片,而是重在调侃、诙谐视角,将焦点对准小人物、普通人。在中国观众心中,与《虎口脱险》构成双壁的法国二战名片《王中王》,走的同样是幽默讽刺路线。
交流中,两国专家认为,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欧亚大陆两端的法国与中国有着类似的对德对日抗争历史。中法两国虽然身处不同的战场,却都肩负着反抗侵略、争取自由的共同使命,如今共同弘扬珍爱和平、反对战争的正确二战史观。汪朝光表示,电影是社会现实的深刻反映,中国电影人战时拒绝合作与日本战争电影受到冷遇,表明日本在中国借助电影宣传其侵略性意识形态的失败。
天创优配提示:文章来自网络,不代表本站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