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人物小传】
张明明,1985年出生,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仁济医院消化科主治医师、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上海市消化疾病研究所副所长,今年获“银蛇奖”二等奖。
在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仁济医院、上海市消化疾病研究所的实验室,显微镜下的病理图谱仿佛一片未知的星辰大海。张明明正是在这片“星空”中,寻找破解炎症性肠病(IBD)密码的人。五年前,他在这片“星空”中的一项重要发现照亮了全球消化领域的一角——研究成果登上《自然》杂志。这一科学发现仅仅是他的职业“高光时刻”之一。
40岁不到,以第一作者或通讯作者身份已发表SCI论文15篇,以独立第一作者发表在《自然》等顶刊上的论文,总被引用2200余次,张明明无疑是年轻医生中的佼佼者。追溯他20多年的医路生涯,从上海到纽约,再回到上海,他的旅程始终围绕一个圆心:为饱受炎症性肠病困扰的患者,寻找真正的“解钥”。
发现之光
炎症性肠病(IBD),大部分人没听说过这病,简言之,肠道“发炎”,但这远不足以描绘患者的痛苦。炎症性肠病有两大主要分类——克罗恩病、溃疡性结肠炎,病因不明,临床表现就是肚子疼、拉肚子,重度患者一天腹泻十多次乃至几十次,根本离不开马桶,严重影响生活。
“IBD起病隐匿,不易察觉,很多患者首诊时肠子溃疡、脓肿,肠间形成内瘘或肠皮瘘,肠液从腹部破溃处流出来,患者很痛苦,只能把烂掉的肠子切掉,但它容易复发,只能再切肠子,肠子越切越短……”张明明感慨,炎症性肠病在我国还是少见病,但我国人口基数大,随着生活节奏加快、饮食不断西化、高糖高热量饮食成为不少人餐桌上的主流,多方面因素交织,炎症性肠病在我国的发病率越来越高,被称为“不死的癌症”。
IBD致病原因不明,那么,有没有办法治疗?最初,医生们给患者用广谱的抗炎药治疗,但是包括激素、免疫抑制剂在内的这些药物副作用大,有年轻的患者吃了药出现“满月脸”“水牛背”,甚至出现重症感染。最近二三十年,药物不断进展,随着新靶点发现,副作用小的新药逐渐问世。比如JAK-STAT靶点小分子抑制剂,在我国已纳入医保,这也是一个百亿美元的巨大市场。
张明明也关注到这个基础研究和临床治疗的焦点,基于前期研究,他带着这个临床课题前往美国霍华德休斯医学研究所/康奈尔大学研究攻关。在美国,他聚焦JAK-STAT靶点,终于发现了调控JAK-STAT靶点的全新分子机制,在此基础上合成了新型小分子抗炎药。2020年,这一成果发表在国际顶尖期刊《自然》杂志上,张明明是唯一第一作者。2021年,该研究成果的PCT国际专利获批。此后,该成果在美国获得300万美金的天使轮融资,用于新药临床实验和推广。
“后续顺利的话,相关药物有望推向临床。”张明明欣喜地说。2021年1月他来到上海仁济医院至今,临床工作之余一直在优化、推进这一成果。
患者之痛
一两行字能说清的科学突破,医者却花费了20多年时光,期间目睹的是患者无尽的痛苦。
“与五年乃至十年前相比,炎症性肠病的治疗可谓突飞猛进。”张明明说,困扰国人的胃癌、肠癌,发病原因和流行病学特点逐渐摸清,比如已发现幽门螺杆菌与胃癌发病有关,提前把这个细菌杀灭,后期胃癌患者就少了,但对炎症性肠病,至今搞不清楚致病原因。
值得一提的是,炎症性肠病在青少年时期高发。“一旦确诊,患者一辈子要与这个病抗争,病程很长,对社会资源的消耗、对家庭的拖累、对自身的生理心理创伤都非常大。”张明明说。
2009年,张明明在南京鼓楼医院从事住院医师工作,接诊了一名克罗恩病患者,这是炎症性肠病中的一种。这名患者30多岁,刚来医院时只有五六十斤,瘦得皮包骨头,老婆天天陪着治疗。
“这个病已经把他的家庭拖垮了,我们想尽办法,给他找治疗方案。他的肠子已经切了又切,营养很难吸收,就靠肠内营养液整日从鼻饲管输到体内‘续命’,每天就看见他提着输液杆,在病房里走来走去……”张明明忘不了走廊里的这一幕,患者好像已经走不出这个“一直在输液”的人生叙事。
多年后回南京,路上有人叫住了张明明。只见眼前的人胖了一圈,就是那名男患者。“我在这里当协警。”交谈中,张明明听到更多好消息,“后来用上靶向药,我已经很久没有复发了。”
“虽然不是我治好的,但我也很有成就感,毕竟是我管的第一批患者,随着大家对这个疾病认识的提高,投入更多研究,他有了新药,改变了疾病走向乃至人生轨迹。”张明明说。
未来之策
不止步于过去,在全国知名的仁济医院消化科,张明明开启新的探索:沿着JAK-STAT靶点,他带领团队探究筛选IBD治疗潜在药物,建立小分子化学合成和菌群产物筛选研究的实验方法和技术平台,揭示靶向JAK-STAT抑制IBD的分子机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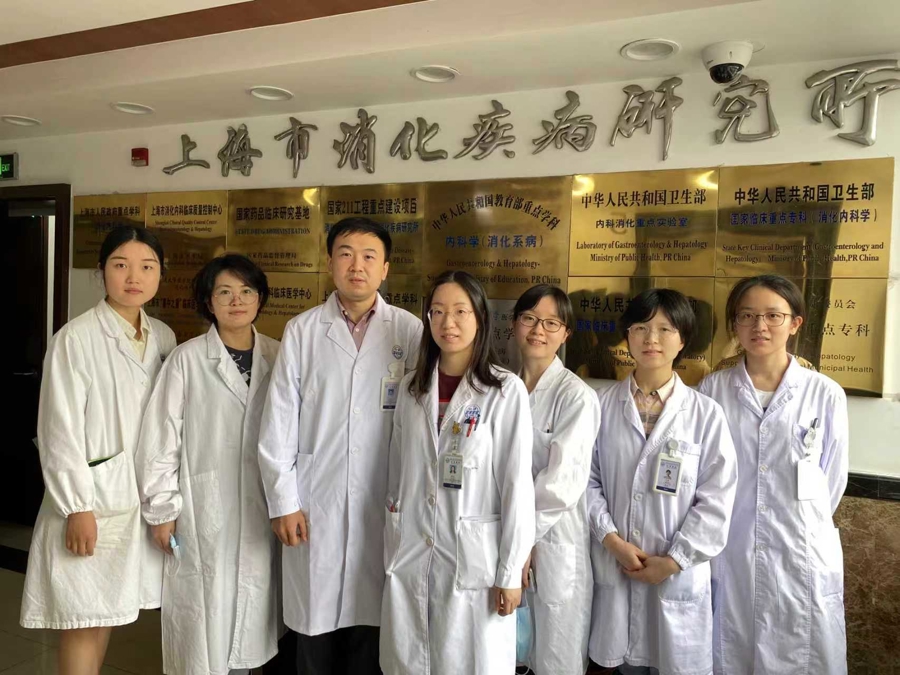
近年,他们把“明星细菌”阿克曼细菌,一种与糖尿病、肿瘤等很多疾病相关的细菌,放在这个研究平台上,最终鉴定出一个新成分。2022年,相关成果在消化病领域顶级期刊《胃肠病学》(Gut)发表,2023年获批国家专利。这种新成分有望成为炎症性肠病的又一新药。
持续探索、医路生花,张明明有股“初生牛犊不怕虎”的劲头。研究生入学面试,也是他确定投入炎症性肠病的一个起点,当时有专家问他:你报这个方向,见过这个病吗?张明明回答:“没有,我就在书本上看过”。
“我就认为搞不清楚原因,才需要我们去投入研究。”张明明说。
“我的太爷爷是当地郎中,家中一直有人从医,这让我自小就觉得治病救人是很高尚的事。在上海,在仁济医院,在消化科,江绍基院士、萧树东教授、房静远教授等消化名家代代传承的医疗和学科氛围更让我坚定了要当一个既懂科研又擅临床的研究型医生,能对临床难题作出探索,让患者最终受益。”张明明说。
天创优配提示:文章来自网络,不代表本站观点。